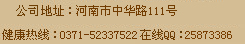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波斯猫简介_波斯猫价格 > 波斯猫品种 > 短经典国王迷上
当前位置: 波斯猫简介_波斯猫价格 > 波斯猫品种 > 短经典国王迷上

![]() 当前位置: 波斯猫简介_波斯猫价格 > 波斯猫品种 > 短经典国王迷上
当前位置: 波斯猫简介_波斯猫价格 > 波斯猫品种 > 短经典国王迷上
国王迷(上)
鲁德亚德·吉卜林
著潘庆舲
译费尔南多?维森特
图
凡和王孙公子称兄道弟,或与贫丐莫逆交者,则为俊杰。
上面引述的这个守则,虽可作为处世待人的圭臬,但要身体力行起来,却又谈何容易。我曾经一而再地与贫丐结交朋友,由于当时环境,我们谁都无法查明对方是不是俊杰。不过,现在我仍然还得和王孙公子称兄道弟,虽然我曾经一度接近过类似下面的这种人物,他也许可以称之为一个真正的国王,并使一个王国——军队、法院、岁入和政策全部为之逆转。但在今天,深恐我的那位国王早已命归西天,如果说我想要得到一顶王冠,那我就得给自己去寻觅了。
事情是从阿杰梅尔开住姆豪的火车上开始的。由于收支预算出现了亏空,迫不得已这才出门远行,搭坐的不是票价只及头等车票一半的二等车,而是确实令人可怕的客货混合车厢,这种客货混合车厢,里面没有软席靠垫;旅客也是五方杂处,不是欧亚混血种,就是夜间长途旅行时令人作呕的土著,或是喝得烂醉如泥、逗人直发笑的游手好闲者。客货混合车厢里旅客从不光顾小吃部。他们自带一包包、一罐罐干粮,向当地小贩买糖块吃,还随便喝路旁的生水。到了热天,为什么客货混合车厢里要抬出死人来,而且平时总是让人瞧不起,原因就在这里。赶上我坐的那节客货混合车厢,恰好是空无一人,直到纳西拉巴德才走进来一个身躯高大、衣着随便的男人;按照客货混合车厢的惯例,我们寒暄后就攀谈起来。他同我一样是漂泊无定,浪迹天涯,但他附庸风雅,爱喝威士忌。他娓娓动听地讲了许多他亲历其境的事情,他曾经深入到印度帝国的僻远角落,以及为了乞食糊口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的惊人经历。他说:“如果说印度全国上下都像你我之辈,连下一天的口粮都还不知道上哪儿去找,那末,国家要支出的岁入就不是七千万——而是七亿整了。”我朝他嘴巴和下巴颏儿望了一眼,不用说跟他有同感。
这样,我们就议论开政治了。大凡游手好闲的人在议论政治的时候,他们总是从事物的底层,亦即生活阴暗面来观察的。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了邮政设施,因为我的朋友要从下一站给阿杰梅尔拍发一个回电,而阿杰梅尔正是你西行由孟买至姆豪的干线上的一个岔道口。我的那个朋友除了吃饭钱八安那?以外已是身无分文,而我由于上面提到的收支预算拮据,根本不名一文。再说,此刻我要到人迹罕至的荒地去,虽然我应该继续和财政部保持联系,但是那里却没有电报局。所以说要资助他,我实在力不从心。
“我们不妨对那个站长吓唬一下,让他马上就发出一个电报,”我的朋友说道,“不过那么一来就得要盘问你和我了,可我这些天来手头正忙呢。你说你过几天再坐这趟车回来?”
“十天之内。”我说。
“你改成八天不行吗?”他说。“我可有急事要办。”
“十天以内我可以打电报给你,如果你认为那样合适的话。”我说。
“现在我一想,他不一定能收到这个电报。事情是这样的。他在二十三日离开德里去孟买。那就是说,他将在二十三日夜里经过阿杰梅尔。”
“但是此刻我要去印度沙漠。”我马上说明来意。
“好,好得很。”他说,“那你就要在马尔瓦尔枢纽站换车,才能进入乔德普尔地区——你非得那么个走法不可——而他将在二十四日凌晨乘坐孟买邮车经过马尔瓦尔车站。那时你赶得到马尔瓦尔站吗?这可不会给你增添什么麻烦的,因为我知道:从印度中部各邦可以采集的东西很少——就算你装作《巴克伍兹曼报》的记者。”
“你老是耍弄那套把戏吗?”我问。
“不止一次啦。可是,当地居民会发现你的,所以趁你还有时间用刀子捅他们以前,就得找人护送到边境。不过,这里说的是我的那个朋友。我一定要捎个口信给他,把我的近况告诉他,要不然他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我请你老兄多多帮忙,但愿你务必准时离开中部印度,赶到马尔瓦尔站跟他会面,并对他说:‘他去南方已有一个星期了。’他会知道那句话里的意思的。他是个蓄红胡子的大汉,他这个人可真了不起。你将在二等车厢里找到他,他活脱脱像个绅士睡在那里,四周围都是他的行李包裹。可你用不着害怕。拉下车窗,说,‘他去南方已有一个星期了。’他一听心里就明白啦。这样,你停留在那里的时间仅仅缩短两天。我,作为一个陌生人,要求你——到西部去走走。”他加重语气地说道。
“那现在你是从哪儿来的?”我说。
“从东部来,”他说,“现在我希望你就老老实实地把这个口信捎给他——看在我母亲和你自己母亲的面上。”
虽然英国人通常不会一提到母亲就心软下来,但由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我几乎要表示赞同了。
“这事实在非同小可,”他说,“我为什么要你去办这件事,原因就在这里——而现在,我知道我可以放心让你去办了。马尔瓦尔车站上的一节二等车厢里,睡着一个红头发的男人。你肯定记得住的。我下一站就下车,我一定留在那里,直到他来了,或者给我送来了我所需要的东西。”
“我一定把这个口信捎给他,只要我赶得上他,”我说,“看在你和我的母亲面上,我就要给你进一言。就是现在千万不要以《巴克伍兹曼报》记者的身份,在印度中部各州到处走访。因为有一个真正的报社记者正在这里到处采访,这样说不定会给你招来麻烦呢。”
“谢谢你,”他直率地说,“那个蠢家伙什么时候才走呢?现在我可再也受不了啦,因为他正在把我的工作给毁了。我要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寡母的情况,向德古姆伯王公?谈一谈,让他吓一跳。”
“那末,他对待自己的寡母又是怎样的呢?”
“当她悬在横梁上的时候,他给她灌满了红辣椒水,还用拖鞋揍得她昏死过去。那是我亲自发现的,因此,唯有我一个人,才敢到邦里去拿封住自己嘴巴的钱。可是,他们想方设法要伤害我,就像从前我在乔敦姆纳敛钱时他们所作所为一样。不过,我说你在马尔瓦尔枢纽站会把我的口信捎给那个人吗?”
他在路旁一个小站下了车,我顿时陷入沉思之中。我不止一次地听说过:有人冒充新闻记者,向一些小的邦政府威胁说要揭发,乘此机会敲竹杠,但我过去从来没有碰到过任何一个像上面那样敛钱的人。他们过着一种艰苦的生活,而且常常是突如其来地死掉了。各地邦政府对可能揭发他们独特的施政方法的英国报纸都很惧怕,于是,他们竭力用香槟酒来堵住新闻记者的嘴巴,或者用四匹马拉的四轮大马车干脆把他们驱逐出境。他们根本不了解,只要压迫和罪恶还没有越过界限,不论是谁,对于各地邦政府内政都是丝毫不感兴趣的,而各地统治者一年到头不是吸毒、酗酒,就是病魔缠身,动弹不得。各个土邦由上帝创造出来,只不过增添了山川如画的景色、老虎和大量长篇累牍的文件罢了。它们是地球上暗无天日的地方,充满了难以想象的暴行,一方面有现代化的铁路和电报,另一方面还处在哈伦·拉希德?的时代。我下了火车以后,就同好几个国王打交道去了。在这八天时间里,我的生活却大起大落,几经变化。有时候我身穿华服,陪伴王孙公子和政界要人,宴饮时手执水晶酒杯和纹银盘碟。但也有的时候,我却躺在地上,用化妆盒当作盒子,随便抓到什么东西,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而且还得喝生水,裹上如同我仆人使用的破毯子睡觉。这是习以为常,毫不稀奇的事啦。
随后,根据我原先约定的合适日期,我动身前往印度大沙漠。夜间邮车把我带到马尔瓦尔枢纽站,有一条由地方当局经营、虽然狭窄得可笑、却是逍遥自在的铁路线,从那里一直通往乔德普尔。来自德里的孟买邮车在马尔瓦尔停留时间很短。我刚进站,邮车才抵达;我正好赶到站台,上了车。这趟列车通共只有一节二等车厢。我放下车窗,低头望着被车上毯子盖没了一半的火红的络腮胡子。那人正在呼呼大睡,他就是我要寻找的人,于是我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胸口。他哼了一声,醒过来了。我借着灯光看见了他的脸孔。那是一个闪闪发亮的大脸盘。“又是车票吧?”他说。
“不,”我说,“我要转告你:他到南方去已有一个星期了。他到南方去已有一个星期了!”
列车开始移动了。那个红胡子的人擦擦自己的眼睛。“他到南方去已有一个星期了。”他又说了一遍,“那正是他所说的傲慢无礼的话吗?他还说过我得给你一些什么东西吗?——反正我不会乐意的。”
“他没有说过。”我说后转身就走,眼看着红灯消失在黑暗之中。天气冷得够呛,因为大风正把砂土都给刮了起来。我登上了自己的车厢——这一回可不是客货混台车厢——就睡觉去了。
那个红胡子的人要是给我一个卢比?,本来我可以把它珍藏起来,作为一件相当稀奇古怪的趣事的纪念品。但我所得到的唯一的酬偿,只是意识到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后来,我暗自思忖:那两个人好像是我的朋友,即使他们凑在—起,冒充新闻记者,那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来;他要是去“抢劫”中部印度或南拉杰普塔纳濒于绝境的一个小邦,说不定会使自己陷入严重的困境。所以说,要对那些想放逐他们的人,凭我的回忆尽可能精确地把他们描述一番,就不免有些困难了。(后来,我就听说,他们终于从德古姆伯边境被押了回来。)
随后,我总算好歹又回到了编辑部,在那里除了每天出报以外,根本没有什么国王之类的事情可说。但因报社编辑部对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物似乎都有吸引力,所以也就很难保持良好的秩序。身在深闺后院的印度小姐派出代表团,前来要求主笔即刻放弃自己全部职责,不要去报道基督徒在一个穷乡僻壤的贫民窟里分发奖品的事迹,有一些上校在结束了戎马倥偬的生涯以后,就坐下来拟定了十篇、十二篇或二十四篇有关资历与选拔的社论提纲,有些传教士想要了解一下,他们作为辱骂人们的工具,很有意见,极想离开,但为什么老是不让他们脱身而去,而且此刻还在诅咒受到编辑部同人特别保护的某个兄弟教会,有一些走投无路的剧团向报社联合声明,他们实在付不出广告费,但从新西兰或塔希提岛?一回来,他们将连同利息把它一起付清;还有一些人发明了专利大风扇牵引器、火车挂钩,以及不易破损的刀剑和轴干,他们来访时口袋里装着说明书,一连好几个钟头向报社同人介绍情况,一些茶叶公司办事人员走进了报社,对撰稿人详细说明他们的计划书;化妆舞会的主办人常常埋怨报社对他们的舞会报道得过于详尽了;一些陌生的贵妇人衣裙窸窣作响,走进来说:“我要许许多多女士名片,请马上印出来。”显而易见,这就是主笔职责的一部分了,甚至闲荡在大马路的每一个流氓,都认为自己应该去报社求职,充当一名校对员。在编辑部里,电话铃声整天都在疯狂地响个不停,一些国王正在欧洲大陆上被杀害,一些帝国却在扬言道:“你也是一个帝国哪。”格拉德斯通先生正在责骂英国自治领,而专替报社送稿件的黑孩子,就像疲惫不堪的蜜蜂一样,正在呜呜地哀叫“卡阿一比,恰伊一哈一耶”(意思是:副本要吧),本子上大部分都是黑糊糊的,如同莫特雷德?的盾牌一样。
不过,这是一年之中兴味盎然的时节。除此以外,还有剩下来的六个月,那就没有人来登门求访了;寒暑表上的度数一英寸、一英寸地往上升高,一直升至玻璃管顶端,报社编辑部里,除了案头的灯光以外,一片黑暗;印刷机一直在转动,摸上去滚烫滚烫;但谁都懒于执笔,写的净是印度山中避暑胜地的趣闻,或者撰写讣告而已。那时候,电话铃声就成为一种恐怖的讯号,因为它会向你报告你所熟悉的男人、女人突如其来死去了。痱子像罩袍似地布满了全身,你还得坐下来写道:“来自库德·詹塔·汗地区报道,疫病稍有增加,此次突然蔓延,纯属偶然性,现经该地区当局大力拯救,几乎已近敛迹。但我们对所述的死亡情事则深表遗憾。”
那时,疫病确实突然发生过,只要记事报道得越少,撰稿人心中也就越安宁。但是,帝国和国王依然如同往日一样自私地尽情玩乐;领班却认为:一张日报在二十四小时内确实应该出版一次;而所有在山中避暑的人们,在他们寻欢作乐时却说;“我的天哪!为什么报纸不能办得更活泼些?我敢说这儿山上发生的事就够多啦。”
那就是不为人们所知道的一些秘闻,正如广告上常说的,“如蒙惠顾,包君满意”了。
正是在那样一个极其不吉利的季节里,报社开始在星期六夜间——这就是说,按照伦敦报纸惯例,是在星期日凌晨——出版本周最后一期报纸。这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因为当铅字排好刚放到印刷机上不久,熹微的晨光就在半个钟头以内使寒暑表上的度数从华氏九十六度几乎骤然下降至八十四度,在那种沁人肺腑的凉意之中——在你开始祈求这种凉意以前,你根本不会知道华氏八十四度在草地上该有多么凉快——一个疲惫不堪的人,就可以安然入睡,趁着炎热还没有把他惊醒。
赶上星期六夜晚,我只要把报纸编好,一放到印刷机上,就算愉快地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不管某一个国王,或某一个朝臣,或某一个名妓,或某一个社区行将销声匿迹,或者得到一部新宪法,或者在世界另一边出现了一些重大事件,报纸为了赶上最新电讯稿,直到最后一分钟,尽可能保留出空白版面。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夜晚,而且又闷热得比六月之夜更叫人透不过气来。西边刮来的热风,正在干得像火绒似的树丛间嗡嗡作响,仿佛马上就要下雨了。不时有一颗几乎煮沸了的水点落下来,像一只青蛙似的在尘土里扑腾着,但我们这些疲乏透顶的人都知道那只不过是假象罢了。倒是印刷间比报社编辑部更阴凉些,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听咔嚓咔嚓地排捡铅字的声响,以及夜枭在窗边的哀鸣声,而那些几乎赤身裸体的排字工人老是在擦脑门上的汗水,嘴里一个劲儿喊着要水喝。那条好像对我们一直隐瞒其内容的电讯稿,直到此刻还是迟迟未到,虽然热风渐渐停息下来了,铅字最后也已经排好了,整个大地依然处在令人窒息的酷热之中,傻等着那条重大新闻。我迷迷糊糊地在暗自纳闷:那条电讯是不是一件大喜事,这个行将死亡的人,或在苦斗中的人们,是不是知道电讯稿迟到以后将会造成的那种麻烦。虽然产生紧张的情绪,除了炎热和忧虑以外,没有其他特殊原因,但是,当座钟的时针指向三点钟,机器飞轮转上两三次,看到一切都已井井有条,就在我说可以开印之前,本来我也许还会尖声叫喊起来呢。
随后,沉寂的气氛被机器飞轮发出的嘎嘎声震碎了。我站起身来要走,。但有两个身穿白大褂的人站在我面前。头一个人说,“就是他!”第二个人也说,“没错,是他!”他们两人哈哈大笑的声音,几乎就像机器声一样震耳欲聋。同时,他们都在擦脑门上的汗水。“我们看见对面马路上有一处灯光还亮着。刚才我们贪图凉快,正躲在小沟里睡觉呢。我就对我身边的朋友说,‘报社编辑部里还有人在办公。让我们走去跟他说说,我们怎样从德古姆伯邦被撵回来的。’”说上面这些话的,是他们中间个子较小的那个人。他正是我在姆豪列车上遇到过的那个人,而他的同伴就是马尔瓦尔枢纽站上的那个红胡子。这个人的眉毛和那个人络腮胡子,我绝没有认错。
那时我可不太高兴,因为我心里正想去睡觉,不打算跟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嚼舌根,“你们要想干什么呀?”我问。
“办公室里挺凉快,同你闲扯上半个钟头,好吗?”那个红胡子说。“我们都喜欢喝一点儿——反正那个合约还没有开始生效,皮奇。所以你用不着东张西望——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忠告。我们并不缺钱。现在我们只是请你赏个脸,因为我们发现是你叫我们在德古姆伯上了当。”我从印刷间走到四壁挂满地图的令人窒息的办公室,那个红胡子来回搓着自己的双手。“妙极了,”他说,“这算是找对了地方啦。现在,先生,让我向你介绍一下,皮奇·卡内汉大哥,就是他,丹尼尔·德雷沃特二哥,就是我,关于我们的职业嘛,介绍得越少越好,因为我们活到现在,各式各样活儿都干过。什么士兵,水手,排字工人,摄影师,校对员,街头传教士,而且还当过《巴克伍兹曼报》记者,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报社正需要一个记者。卡内汉并没有喝醉酒,我也是那样。乍一看,你就知道这话一点儿都不假。这就不会使你把我的话给打断了。我们每人要向你拿一支雪茄烟,你对我们就会有所了解。”
于是,我察颜观色了一番。那两个人绝对没有喝醉,所以我就给了他们每人一杯不冷不热的白兰地苏打水。
“好,好极了,”卡内汉眉毛一扬说,随手抹去了大胡子旁边的白沫。“现在就让我谈吧,丹?。整个印度大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什么锅炉装配工,火车司机,小包工头等等,样样杂活我们都干过了,我们的结论是;在我们这样的人看来,印度这个地方还不够大呢。”
他们两个对那间办公室来说,当然是太大了。当他们坐在那张大桌子跟前的时候,德雷沃特的大胡子似乎占去了半个房间,卡内汉的两个肩膀则占去了那剩下的半个房间。卡内汉继续说下去,“这个国家的资源并没有完全得到利用,因为它毕竟是归他们所统治的,所以就是不让你去碰它一下。他们把他妈的所有时间都花在统治上面了,你想想要举起铁锹,削凿岩石,勘察石油,或者干类似那样的事情;所有地方政府必定要说:‘别管它,让我门来管理。’所以说,事实上就是那样,我们只好不去管它,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那里,你可以独来独往,好像是自己的天下一样。我们可不是微不足道的人,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害怕,就是喝酒例外,为此,我们就签订了一份合约。所以说,我们将要到外地去当国王了。”
“去当由我们亲自掌权的国王。”德雷沃特喃喃自语道。
“哦,那当然啦,”我说。“你们一直头顶烈日,到处漂泊流浪,此刻正好赶上一个暖洋洋的夜晚,不妨睡一觉,对这个怪念头再好好想一想?还是明天来吧。”
“我们既没有喝醉,也没有中暑,”德雷沃特说,“这个怪念头我们反复考虑了已有半年时间。而且还要查阅许多书籍和地图集。我们的结论是:在当前世界上,可供两个铁腕人物瓜分的,只有一个地方。人们都管它叫卡菲里斯坦。照我的估计,这个地方位于阿富汗右上角顶端,离白沙瓦不超过五十英里。在他们那里,异教徒崇拜的神就有三十二个,而我们俩就要成为第三十三个神。那是一个崇山峻岭的国家,但是那一带的女人却漂亮透顶。”
“可是话又说回来,那正是合约规定所禁忌的,”卡内汉说。“一是女人,二是美酒,丹尼尔。”
“我们知道的通共就是这些,可惜那个地方谁都没有去过。听说那里的人们爱打仗,所以,凡是人们爱打仗的地方,谁只要懂得如何训练士兵,总能当上国王的。我们打算到那个地方上,不论我们找到的是哪一个国王,我们就对他说:‘你要把你的仇敌消灭掉吗?’接着,我们就会指点他如何训练士兵;因为搞那个行当,我们最精通也没有啦。随后,我们就把那个国王颠覆掉,篡夺了他的王位,建立一个新王朝。”
“你越过边界还不到五十英里,恐怕早就被人斩成肉酱了。”我说,“你必须经过阿富汗才能到达那个地区。那里极目望去,都是崇山峻岭,冰川壁立,连英国人都裹足不前,视为畏途。那里的人完全是蛮夷之邦,你们即使到了那里,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来。”
“那可差不离呢,”卡内汉说。“不过,你要是认为我们有点儿痴头痴脑,这才更叫我们高兴呢。现在我们上你这儿来,就是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读一本有关它的书,再让我们查看一些地图。你尽管说我们都是傻瓜蛋,只要把你的那些书给我们看看就得了。”他转过身来指着那些书柜。
“你们真是那么正经八百的吗?”我说。
“有—点儿呗,”德雷沃特温和地说。“你有最详细的大地图,即使卡菲里斯坦在那上面还是一大片空白,以及不管你还有哪些书,都给我们看看吧。书我们都还看得懂,尽管我们文化程度很不够。”
我把那张比例为每英寸等于三十二公里的印度大地图和两张篇幅较小的边境地图都打开来,还把英国大百科全书中字首为INF—KAN的那一大本书也搬下来了。于是,他们两人就查阅起来了。
“看这里哪!”德雷沃特把大拇指摁在地图上说。“往上可以通到贾格达拉克,皮奇和我都知道那条路。当年我们跟着罗伯恃的军队到过那里。我们必须通过拉格曼地区,再往右拐弯,才能到达贾格达拉克。随后,我们进入出区——高度是一万四千英尺到一万五千英尺——那个地方冷得要命,但从地图上看好像还不算太远。”
我把伍德著的《乌浒水河源考》一书递给了他。卡内汉就埋头啃那部大百科全书去了。
“他们那里人种混杂。”德雷沃特若有所思地说,“这么一来,我们就没法了解他们各部落的名字了。部落越多,他们越要打仗,对我们就越有利啦。从贾格达拉克到阿香格。嗯!”
“不过,关于这个国家的所有资料,只是概括介绍,很难说得上十分精确。”我不以为然地说,“至于这个国家究竟怎样,老实说,谁都说不上来。这里是联合后勤研究会的档案材料。念一下贝留的意见是什么。”
“贝留净是吹牛呗!”卡内汉说,“丹,他们都是异教徒,简直多如牛毛,但这本书在这里却说:他们认为同我们英国人有血亲关系。”
我抽着烟,他们两人则在浏览雷弗泰和伍德的著作,以及地图集和大百科全书。
“你等着也白搭,”德雷沃特彬彬有礼地说。“现在大约四点钟了。你要是想去睡觉的话,我们就会在六点钟以前离开,反正我们不会把什么报纸都偷走的。你用不着在这里坐等。我们两个疯子从来不做缺德的事。明儿晚上你到旅店来一趟,我们就跟你挥手告别啦。”
“你们真是两个傻瓜蛋呀,”我回答说。“你们一到了边境,就得碰壁而归,要不然你们一踏上阿富汗国土,就被吃掉了。你们去那个地方需要钱呢,还是要推荐介绍一番?下个星期我可以帮助你们找个事由。”
“下个星期我们自己的活儿还忙不过来呢,谢谢你。”德雷沃特说。“看来要当一个国王,可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们一旦把我们的那个王国整治得井然有序,就会通知你。你就可以来匡助我们治理那个王国。”
“两个疯子还签订过那么一个合约呢?”卡内汉带着几分矜色说,并拿出半张油腻腻的信纸给我看。那半张信纸上写着如下条款,我照看抄录下来,堪称天下奇闻:
立约人谨遵守以下各条款,但愿上帝作证,阿门。
第一条立约人将共同解决以下问题,即是:当上卡菲里斯坦国王。
第二条此问题一旦获得解决,立约人应拒绝任何美酒和女人(不论是黑种、白种、或棕种),以免跟任何有害的人种发生混杂现象。
第三条立约人举止态度应保持尊严、审慎,如果其中有一人遇到麻烦,另一人仍应留在他身边。
立约人
皮奇·托利弗·卡内汉(签名)
丹尼尔·德雷沃特(签名)
(上述两人均为赋闲绅士?)
“最后那一条大可不必写上的,”卡内汉不觉有点儿脸红地说:“但看来也是一种惯例吧。至于游手好闲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是知道的——不过,丹,我们只要一出印度国界,就不算是游手好闲的人啦——如果我们不是一本正经的话,你说我们还会签订那么一份合约吗?我们所以要禁忌美酒和女人这两个东西,就是为了使人生变得更有意义。”
“如果你们要去进行这样愚蠢透顶的冒险,你们真的活腻了,不乐意再活下去了。千万别放火烧报社编辑部,”我说,“九点钟以前,你们通通滚出去。”
我离开的时候,他们还在仔细观看各种地图,并在那张“合约”背后记下一些要点。“明天务必来旅店哪,”——这就是他们的告别词。
孔哈森旅店是一座四方形的大房子,真是藏污纳垢的场所,来自北方的一群群骆驼和骡马,正在那里装卸货物。中亚细亚所有各族的人在那里可以说应有尽有,但十之八九还是来自印度大陆的人。巴尔赫人和布哈拉人在那里一碰到了孟加拉人和孟买人,总是少不了暗算对方。在孔哈森旅店,你可以买到小马驹、绿松石、波斯猫、马褡裢、肥尾羊和麝香,而且还可以不费分文,搞到许多稀奇百怪的东西。第二天下午,我就往那个旅店走去,想看看我的那两个朋友是不是有意信守自己的约言,还是喝得酩酊大醉,此刻早已倒下了。
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祭司,手里一本正经地捻着一个儿童玩的纸褶旋螺,高视阔步地向我走过来。后面是他的仆人,这会儿弯着腰在装载一大篓泥塑玩具。当这两个人正在给两头骆驼装货的时候,旅店里的客人都直瞅着他们,不断发出尖厉的笑声。
“这个祭司是个疯子,”一个马贩子对我这样说。“他就要到喀布尔去,把这些玩具卖给埃米尔?。赶明儿他要么是被尊奉为座上嘉宾,要么就是脑袋落地。今儿早晨他才到这里,打这以后,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疯疯癫癫的。”
“糊涂鬼自有老天爷照应哪,”一个脸颊扁平的乌兹别克人用蹩脚的印地语在结结巴巴地说话。“他们未卜先知,能预言未来一切吉凶祸福。”
“我的商队刚进入离那个山口不远的地方,就被希恩沃里斯人搞掉了,难道他们也都能预言到吗!”一个尤苏富扎伊商人咕哝着说,原来他是拉杰普塔纳一家商行的代理人,正在越过边界的时候,他的货物全被落入凶恶的强盗手中,现在他的不幸遭遇却成为赶集人的笑柄。“喂,祭司,你从哪儿来的,你又打算上哪儿去呢?”
“我刚从鲁姆来,”这个祭司一面挥动他的纸褶旋螺,一面大声嚷道:“是从鲁姆来的,叫许许多多的魔鬼吹一口气,我就飘洋过海给刮来了?!啊,小偷、强盗、撒谎的人,皮尔·汗为猪、狗祝福,此外还有作伪证的人!有谁带领这个叨受神恩佑护的人到北方去,把这些法力无边的神符通通卖给那个埃米尔吗?赶明儿骆驼四肢不会擦伤,儿子们不会生病,但愿让我加入商队的先生们出门远行期间,他们的妻子仍然忠于自己的丈夫。有谁助我一臂之力,让那个罗尔人的国王趿着银鞋跟金拖鞋走路呢?但愿皮尔·汗保佑他马到成功!”他扯开了他那宽大的布袷袢的下摆,踮起脚尖,在拴上了套的骡马行列中间转来转去。
“有一支商队将从白沙瓦起程,二十天以后到达喀布尔,赫兹鲁特,”这个尤苏富扎伊商人说道。“我的几头骆驼跟他们一块儿走。但愿你也一起走,这会让我们走好运呢。”“即使此刻走我也乐意!”那个祭司大声嚷道。“我将跨上我的那些带翅膀的骆驼,一天就到白沙瓦!喂!哈利尔·米尔·汉,”他冲着他的仆人大声吆喝道,“快把骆驼牵出来,不过,让我先骑上我自己的那头骆驼。”
那头骆驼一跪在地上,他纵身一跃,骑在它的背上,就转过身来冲我大声喊道,“你也上路走一程吧,萨希布?,我就会卖给你一道符咒——凭这道符咒,你包管当上卡菲里斯坦的国王。”
那时,天刚破晓,我跟着两头骆驼走出了旅店的大门,一直走到大路上,那个祭司这才停住不走了。
“关于那个事儿,你到底有什么高见?”这时他用英语说话了。“卡内汉不会说他们的黑话,所以我就叫他做我的仆人。他做得真是顶呱呱的。我在国内到处流浪,已有十四个年头,可不是一无所得呀。我说起那些黑话来,不是很干净利落吗?我们将在白沙瓦搭上一支商队,直至到达贾格达拉克,以后,再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毛驴,把我们的骆驼给换下来,下一步就打进卡菲里斯坦去。把纸褶旋螺送给那个埃米尔,我的老天哪!把你的手伸进那些骆驼的鞍囊,说说你摸到了什么东西。”
我摸到了一支马提尼枪的枪托,以及其他同样的东西。
“通共二十支,”德雷沃特沉着地说。“通共二十支,还有相应的弹药,都藏在纸褶旋螺和泥娃娃的底下。”
“万一你和这些东西都被人截获了,但愿老天爷会帮你的忙,”我说。“一支马提尼枪的价值,在帕坦人?那边,就等于枪支重量的白银哪。”
“本钱就有一万五千卢比——每一个卢比,我们都是通过乞讨、借贷,或者干脆偷窃才得到的——一股脑儿都押在这两头骆驼身上了,”德雷沃特说。“我们可不会被人抓住的。我们将要跟随一支定期的商队通过开伯尔山口。一个可怜巴巴的疯子祭司,谁敢碰他一碰?”
“你想要的每件东西,现在都得到了吗?”我惊骇不止地问。
“还没有呢,不过我们马上就要得到了。老兄,给我一件纪念品,表表你的心迹。昨天你帮了我的忙,还有在马尔瓦尔的那一次。俗语说得好,你准定拿到我的半个王国。”我从我的表链上摘下一只漂亮的小指南针,就递给了那个祭司。
“再见,”德雷沃特一面说,一面小心翼翼地向我伸过手来。“在最近那么几天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同一个英国人握手。卡内汉,跟他握握手。”正当第二头骆驼从我身旁走过时,他大声嚷道。
卡内汉俯下身子来同我握手。随后,那两头骆驼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路走过去了。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禁不住暗自纳闷。他们经过乔装打扮以后,我竟然连半点儿破绽都看不出来。在旅店的这一幕表明他们跟当地人想的完全相同。所以说,正是机会凑巧,卡内汉和德雷沃特满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在阿富汗各地到处漂泊流浪了。可是,再往远处走,他们就会找到死亡,而且肯定是一种可怕的死亡。
十天以后,我有一个老乡,从白沙瓦给我捎来了当天的新闻消息,他在信上这样写道;“最近这里发生了令人捧腹大笑的趣闻,原来有一个疯子祭司,照他的估计,就可以把那些花里胡哨的小饰物说成是法力无边的符咒,通通卖给布哈拉埃米尔殿下。他从白沙瓦出境后,就加入了前往喀布尔的第二支夏季商队。商人们都觉得喜出望外,因为他们有迷信思想,认为有了这些疯疯癫癫的家伙结伴同行,准会使他们走好运。”
那时,他们两人早已越过了边界,我还为他们祈祷过平安,可是,就在那天夜里,有一位名副其实的国王在欧洲驾崩,需要在报上刊登一条讣告。
世界就像飞轮似的按照相同的周期在不断地旋转着。夏天去了,冬天来了,总是那样周而复始,循环不息。那份日报还在继续出版,而我也并没有离开它。到了第三个夏天,正是一个炎热的夜晚,晚上要出一期报纸,紧张地等着从世界的另一端发来的新闻电讯稿,其实,这条新闻电讯就跟从前发生过的无分轩轾。有好几个大人物已在过去的两年里与世长逝,机器转动时发出的是更多的噪音,而且报社花园里一些树木,也不见得长高了几英尺。不过要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也就是那些罢了。
我走过那个印刷间,正如我早已描述过的那一幕情景,恰好又浮现在眼前。由于心中紧张不安,比两年以前还要强烈,我觉得天气也就更加炎热难受了。到了三点钟,我大喊一声“开印”,转身要走,就在这当儿好像有一个人影儿爬到我椅子旁边。他俯下身子,好像弯成一个环儿,脑袋深陷在两个肩膀之间,而且,他一前一后正在挪动自己的两脚,那姿势简直就跟狗熊一模一样。我几乎看不清他是在走路呢,还是在爬行——这个衣衫褴褛、唉声叹气的残废人,冲着我直呼其名,大声嚷道现在他已经回来了。“你能给我一点儿喝的吗?”他呜咽着说。“看在老天爷面上,给我一点儿喝的!”
我走回编辑部办公室,那个人带着痛苦的呻吟跟在后面,于是我就把灯打开了。
“你不认得我了吗?”他气喘吁吁地说,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里。于是,他的那张奇形怪状的脸,和一头乱蓬蓬的灰发,就朝着灯光转了过来。
我目不转睛地直望着他。那双一英寸宽黑带似的眉毛,记得从前我在哪里目睹过的,可是此刻反正我说不出那是在什么场合了。
“我可不认得你,”我一面说,一面把威士忌送给他。“现在你要我干什么呀?”
他咕嘟一声就一口喝干了,尽管这时天气炎热得令人窒息,但他浑身上下还是在哆嗦着。
“现在我可回来了。”他又说了一遍,“我当过卡菲里斯坦的国王——我和德雷沃特——我们俩都是正式加冕过的国王呀!这个事情从前我们就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定下来的——当时你坐在那里,还给我们看了好些参考书籍。我就是皮奇——皮奇·托利弗·卡内汉,打那个时候起,你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我的天哪!”
我不由得大为惊讶。于是,我就向他表示同情。
“这是真的,”卡内汉冷冰冰地笑着说,来回抚摩他那双缠着破布头的脚丫子,“千真万确。那时我们真的当过国王,头上都戴着王冠——我和德雷沃特——可怜的丹——哦,可怜的、可怜的丹,他从来都不肯听人家的忠告,虽然我也没有好好规劝过他!”
“喝威士忌吧,”我说,“你就慢慢来,把你尽可能记得的每一件事情,从头到尾、原原本本讲给我听。当时你们骑着骆驼越过边界,德雷沃特假扮成一个疯疯颠颠的祭司,你就充当他的仆人。现在你还记得起来吗?”
“我还不算是疯子——不过,我马上就要发疯了。当然我都记得。你继续望着我,要不然我的话儿也许就要断断续续连不起来了。你继续望着我的眼睛,什么话都不要说。”
我俯下身子,两眼尽可能眨也不眨地直望着他的脸孔。他举起一只手,放到桌上来,我就抓住他的手腕,一看五个手指弯弯扭扭,好像一只鸟的爪子,手背上还留下一方块凹凸不平的淡红伤疤。
“不,不要看那里。朝我本人看呀。”卡内汉说。
▲英国作家路德亚德·吉卜林(-)
________________
?印度货币名。
?王公,指旧时印度各邦的统治者。
?哈伦·拉希德,是阿拔斯王朝(-)巴格达哈里发,其事迹详见《一千零一夜》。
?印度货币名。
?位于南太平洋一岛屿。
?莫特雷德,是亚瑟王传奇圆桌骑士之一,以奸逆而著称。
?丹,即丹尼尔的简称。
?“赋闲绅士”为作者杜撰,在这里意思是指“无所事事的正人君子”,纯系一种自我讽刺。
?埃米尔,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统治者的称号。
?这位假装疯祭司的冒险家在这里说的所有话语,自然都是疯话,不知所示,因而是毫无意义的,今如实译出,仅供参考而已。
?旧日印度、巴基斯坦对人的尊称,寓有先生、老爷之意。
?印度西北境的阿富汗人。
▲《国王迷》()封面
马尔克斯图书馆
「MarquzLIB」
这是世界上最小的读书会
两个人·面对面读一本书
▼
哪里医院治白癜风比较好台湾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转载请注明:http://www.logistics-info.com/bsmpz/44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