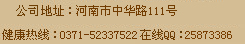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波斯猫简介_波斯猫价格 > 波斯猫性格 > 先生
当前位置: 波斯猫简介_波斯猫价格 > 波斯猫性格 > 先生

![]() 当前位置: 波斯猫简介_波斯猫价格 > 波斯猫性格 > 先生
当前位置: 波斯猫简介_波斯猫价格 > 波斯猫性格 > 先生
纪念黄永年先生九十诞辰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我校召开,与会人员高度评价了我校黄永年先生一生在史学研究、古典文学、目录学、版本学等领域的卓著成就,中华书局总编顾青先生在回忆年暑假听黄先生讲课时,形容其为“美好的夏天”,引起了强烈共鸣。今天专门编选了陆三强老师的回忆文章,以此纪念黄永年先生。
——题记
黄永年教授
文/陆三强
大师是指在学问和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被大家所尊崇的人。
“先生”的字面的意思是表示出生比自己早、年龄比自己大的人,以此外延为有一定地位、学识、资格的人。古汉语“先生”一词是对有学问者的尊称,并非所有人都可称为先生,现在日语、韩语等仍然保留这种用法。
黄永年先生就是有学问而为大家尊崇的人,我们对他所用的就是这种特殊的尊称。
做黄永年先生的学生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四届大学生。那时候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人才奇缺,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曾经有过辉煌的五届同堂。一九八四年夏,主管学生工作的副系主任裴让先生用他那天水口音跟我谈话: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想教学有你的学教,想搞行政有你的行政干,想从事科研有你的科研做。由于崇尚学问,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校。毕业方案一宣布:教育部陕西师范大学。老师告诉我具体是古籍整理研究所。那会儿我懵懵懂懂,真不知道自己想干啥,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啥,完全不懂得职业设计,整个就是听从组织安排了,连古籍整理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倒是一班的许彦政同学知道,还给我看一本教育部古籍整理工作文件汇编。上面有各高校古籍所机构设置和负责人,有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还看到有史念海、高元白、霍松林、黄永年等人的名字。
前排右起:毛双民、傅璇琮、史念海、黄永年、贾宪保
后排右起:赵望秦、胡宝华、孙永如、唐亦工、陆三强
到人事处报了到,我才知道学校的古籍整理研究所经教育部批复已于一九八三年就成立了。目前所长霍松林,编制在中文系,两位副所长黄永年、周炜,编制分别在唐史研究所和科研处,只有我一个正式编制人员。到科研处找周炜副处长报了到,他让我回家过暑假,开学再来。新学期开始后,周炜老师给了我三把办公楼三层三间办公室的钥匙,并说改日带我去见霍老师、黄老师。手握三个办公室的钥匙,把房子打扫了又打扫,在兴奋、忐忑中期待着去见人生中“我的第一个上级”。
秋日的一个下午,周炜老师带我去见霍老师,霍老师虽没给我们上过课,但他曾任副系主任,在唐诗讨论会上见过,简单介绍后我们即离开了。接着带我去见黄老师,还说他要考我。心中十分紧张,对古籍整理毫无概念,不知如何应考。跟着周老师来到黄先生家,周老师对黄先生介绍说:这是刚留校到所里的小陆。我赶紧说:黄老师好!他们二人说了几句公事,周老师就回处里办公了。先生靠在藤圈椅上,面带微笑看着我,感觉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严厉和学究。我端坐在门边的椅子上,脑子里快速过电影,回放着放假前在对门宿舍看的许彦政那本古籍整理文件汇编的内容,想着不知先生会考问我什么。大概看出了我的紧张,先生用他那江阴口音的普通话问我:中学在哪里读的,家里有些什么人,中文系都开些什么课呀,读过哪些书之类的。这时我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一下轻松了,就随便聊开了。七七八八地说了我都学了哪些课程,读过哪些作品。一开始我侃侃而谈,先生也边听边问。当我津津乐道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时,先生皱起了眉头,大不以为然。随即讲述了民国时中文系或叫国文系如何讲课、怎样诗史互证解决实际问题。那时文史相通,陈寅恪、缪钺先生都是同时应聘中文系历史系,或一年在中文系,一年在历史系。大概看我脑子也还算清楚,不是只看“三老”的所谓通史,还读过些正经史料,知道些史实和掌故。便说: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学生了,以后我开的课你都来听,就称呼我黄先生吧!
打这儿起,我便入了黄门,成了黄先生的学生,跟黄先生工作、学习、听课,一跟就是八年,直到一九九二年到出版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八年中有六年坐黄先生对面,和黄先生朝夕相处。我或者与黄先生谈天说地,或者听黄先生讲课,而黄先生或者指导我读书,或者给我改文章。离开了古籍所,先生仍然认我这个学生,项目继续做、文章接着给改,先生出的书仍一本本送……
几十年来我始终是先生的学生,但最终也没能继承先生的衣钵。遇良师不学,这成了我人生的一大遗憾!
在我眼中:
先生一个严厉的人……眼里揉不得沙子。看不惯的事一定要说要管!学校办公楼走廊和厕所的长明灯是每天必关的,学生食堂门口长流水的水龙头也是必关的,这些都是要批评的!学校发的文件中把“副校长”“副教授”的“副”打印成“付”,也会找到校长办公室去教育一番的。
先生是一个有情趣的人……热爱生活。喜欢钢笔、打火机、手表,喜欢吃西餐、巧克力,喜欢猫。那几年师大院子里老鼠多,先生怕家里善本书被老鼠嗑了,一直想养猫。韩茂莉带来一只刚出生不久黄色波斯猫,先生非常高兴,直说他的书可以不怕老鼠了。那猫本事极大,经常沿着高高的书柜顶端蹿来蹿去,一九八六年是农历丙寅年,先生就给猫起名寅寅。她一直陪伴了先生很多年。后来还有一只花的娇娇是她的“孙女”,也陪先生到最后。波斯猫毛长而厚,到了夏天,又长又厚的毛总是打结,而且生虱子。猫身上长了虱子,还往先生身上蹭,弄得他不胜其扰。先生是一爱干净整洁的人,怎能让爱猫难受着?于是为此颇为操心,又是买药,又是托人买一种防虱的项圈,还要经常给猫洗澡。有一次跟我说:这个洋种猫,野性十足哦,蛮劲极大,为她洗澡,她不干,獠牙会把手咬个窟窿!我听了大为担心,可看先生的表情,虽说“恨恨”地咬牙切齿,其实流露出十分的疼爱和喜欢!从此以后,过不多久,我就去先生家帮着给猫洗澡。老人家一边在旁边走来走去,一边告诉我们干这干那,有时还想亲自下手。我负责抓住猫爪,使其不能乱动,寿成师兄施洗。洗完后要用浴巾包上吸干猫身上的水分,还要用吹风机把毛毛吹干吹开。洗一次澡,就像一次战斗!后来这洋猫越长越大,蛮劲也越来越大,给她洗澡有时还得再加上李成甲同学才能一起完成。这猫没事就在沙发上练习捕鼠,眼睛瞪着前方的假想敌,前爪在沙发上往后刨几下,便奋力向前冲去,把家里的沙发面抓得都是窟窿眼。大家不胜其苦,我搞不清先生却为何那么喜欢猫,也许我是那种寡情少趣的人吧!有一年冬天,先生早上来晚了,却兴奋地讲,寅寅生小猫了。原来寅寅那几日晚上总是卧在先生脚底的被子上睡觉,搞得先生都不敢乱翻身,怕影响了这位“孕妇”。那天早上竟然生在被子上了,一窝五只小猫!先生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赶快帮她收拾,给小猫找可以安身的地方。真是有情趣!
先生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一生博览群书、博闻强记。看书过目不忘,从不抄卡片,史料全在心中,用时一翻书就能找到。但不要以为先生只看正经学术书,当代小说也照样看。所里订的报刊由他去取,就为了先睹为快。《当代》《收获》《十月》都看,张贤亮的《绿化树》、莫言的《红高粱》,老人家都看过,而且有自己的看法。先生经常告诉我们:你们晚上要是睡不着觉,放一本《史记》或者《通鉴》在枕头旁边,睡着看嘛。你看,说得有多轻松!有时先生感冒了,不能坚持办公,就找本有趣的书回去边休息边看。你不要以为是什么好玩儿的小说、散文,都是你我认为的严肃书。那时所里刚买了些港台书,一次先生说下午不来,在家休息,让我到资料室为他取一本联经版的胡颂平编著的十卷本《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要最后一本。还告诉我,从后往前看的好处:越近的事情越熟悉、越清楚、越容易看。第二天先生来了就给我讲胡适先生的往事,头头是道,这样的书也能当小说看,真是让我开眼了!和我聊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在上海、苏州旧书肆上见到的善本书,遇到哪个师傅,细述每个书店的每一种书,包括书店来历、位置、经营特色以及书名、版本、品相、册数、价格乃至摆列状况。二十多年前的事,仿佛就在眼前。胡梦琪写毕业论文,研究吴梅村,遇到一条史料,不知何处去查。先生告诉她楼上资料室哪个架子上有本什么书,大致在后半部分有。胡梦琪上去查,不一会儿下来,竟然找到了。这都是我亲历的事情,绝非神话!
先生是一个寂寞的人……晚年无人可以切磋、无人可以聊天,眼神里流露出寂寞而无奈。他告诉我:老了,夜里睡不着,想找点什么书来翻翻,可是,现在这些书和文章,水平能达到陈寅恪先生那样的好像也没有。老朋友一个个走了,周绍良、启功先生相继去世,遇到问题无人可以请教、无人可以聊天了。于是,我请他再给我吟唱唐诗,吟李商隐的诗,吟白居易的诗,就像当年在办公室和我聊唐诗时吟唱的,低回婉转、吴音喃喃,很美妙,像仙曲。我便经常买一些好玩儿的书给他送去,诸如重新出版的唐瑜的《二流堂纪事》、夏衍的增订本《懒寻旧梦录》等,以解寂寞。
先生是一个精神和理念与前辈学者相通的人,虽受的是新式教育,但骨子里更接近老学者,打通文史,兼及古今。
先生是最后的通人学者,堪称大师!
大师已去,再无先生!
先生去世之后,门生故旧、喜爱先生学问的人写了大量回忆先生生平、阐述先生学问、评价先生学术贡献的文章,我便随手加以收集和整理。今年是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作为学生,理当为先生做点儿什么。于是就想编一部反映先生学术思想,总结先生学术成就,论述先生学术风格,评价先生学术影响,以及记载有关先生个人经历、人品、嘉言懿行的文集。
这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树新义室学记:黄永年的生平与学术》,所收文章,依据内容,略作分类:第一部分是先生自述小传、治学经验及学术总结,第二、三部分是对先生的回忆和追述文字,第四部分记载了先生的逸闻趣事,第五部分总结先生的学术贡献,第六部分是先生主要著作的书评,第七部分杂忆先生的访书藏书,最后附录先生的生平简谱和著述简目。《学记》收录了学生对先生为人为学的回忆,其中大都亲受其教,也有少数并未受教于他或未曾谋面,但都认真读过他的书,对他有所间接了解。先生自述学术历程,同侪和门生故旧以切身体会来表达对先生治学和生活情景的回忆,不仅使我们对其学术精神感同身受,还能更深刻地了解学风和时代的变迁。
在《学记》的编选过程中,得到先生亲人、学生等的大力帮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社长刘东风、大众分社社长郭永新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编辑、校对人员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隆情厚意、感荷不已!
《树新义室学记》收集了自先生去世以来回忆黄永年先生为学、为师高风亮节的文章,概述先生学术思想、总结其学术成就、评价其著述的文章,记述先生论学要旨的文章,对弘扬先生为学为师的优秀品行、了解先生谨言笃实的学风、促进学术发展大有助益。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张寿平、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沈津、复旦大学教授张伟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彦弘、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张懋镕、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等联袂撰写、深情怀念!
本书主编陆三强,未来出版社总编辑
史念海先生若是把我们交给这样的老师来调教,未来几年的学习生活,不知会何等恐怖。初听先生讲课,更进一步加重了这样的畏惧。从第一堂课起,先生对那些空泛虚假“学术”的贬斥,就滔滔不绝于耳,其疾言厉色的程度,我背地里一直是用“咬牙切齿”来形容。勤奋以至于忘我,严厉而近于苛刻,这便是我对先生的第一印象。事实上,这在一定意义上,也确实是先生一以贯之的作风。
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
黄永年先生文章中的论点容有见仁见智之处,但是,他的论证所体现的运用文献学知识于历史考证的方法则堪为治史者的典范。他所作出的考证,总能从众人熟悉的材料里,寻幽探微,推陈出新。由于作者在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上的深厚功底,使他对史实的考证有更充分的说服力。从史源上澄清被旧史歪曲的历史事实,也成为黄永年先生研究唐代政治史的一个显著特点。
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
黄兄永年与我同班,且共坐一席。其入吕师之门先于我,所闻于吕师者多于我,其经史目录、考据诸学皆胜于我。其博闻强记,更非我所能及。每逢假日,永年辄邀我同逛常州城内之旧书铺,为我指点旧籍(木刻线装书)之版本与其优劣。一日,我在永年家,适童书业先生来访,因知童为吕师门下高第,时正与顾颉刚合辑古史辨。永年一高中学生而已为当世学人所器重。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张寿平
黄先生是国内的唐史研究专家,也是一位古籍版本研究的重要学者,他是前辈,四十年代末就涉足古籍版本这个领域里了。我以为黄先生的版本目録学的功底很深厚,虽然他自己说是“其实只能算是自学出身。”而实际上他在这方面的学识以及版本鉴定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当今国内各大图书馆的所谓“专家”。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前善本室主任沈津
晚上去宾馆里看他,老远就见他背着手在房间门口踱步,一会儿踱出来,一会儿又进去,步态煞是轻盈。我第一次见他这样,觉得很好玩,忙走过去;他愈发得意,连说:“开心,今天开心!抓着辛德勇帮我刷书!”德勇先生坐在门里边,一面拿一个大棕刷飞快地刷着书,一面嘴里念念有词地回应着黄先生的调侃,动作和语调都特别地飞扬。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神往的一幅“得书图”。
复旦大学教授张伟然
我们发现黄先生研究政治史的一些特点:首先,他十分重视对历史真相的抉发。其次,他对政治史的分析,主要是从统治集团内部(或上层统治者)的矛盾斗争着手的。第三,由于黄先生在版本目录学和古籍校勘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所以在对一些不同记载的辨析时,多能从版本流传方面校正记载的岐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彦弘
有人说,黄先生脾气不好,爱骂人,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的耳根太软,早已习惯了催眠曲,稍微有点尖利的声音,就受不了了。中国的学术界,不缺乏赞歌,少的就是诸如黄先生的“骂声”。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张懋镕
先生十分健谈,说起话来不徐不疾,却总是滔滔不绝,诙谐风趣,嬉笑怒骂,真知灼见层出不穷,听来或振聋发聩,或如沐春风。我至今记得先生在课堂上的“夸口”:“我不是吹牛,凡是重要典籍的主要版本,我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那份自信,还带有一种孩子气的天真与骄傲,就如同孩子向同伴夸耀自己的宝贝。后来我才知道,先生是真的藏有宝贝的。我曾问他,家藏了多少善本?先生哈哈一笑:“我可以讲给你听,但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
陆三强,陕师大80级中文系,年毕业留校,在古籍研究所工作,年到学校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年调到未来出版社,现任未来出版社总编辑。
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sh)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logistics-info.com/bsmxg/bsmxg/141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