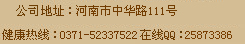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波斯猫简介_波斯猫价格 > 波斯猫简介 > 墨香文学第十八期飘短篇小说常忆那年
当前位置: 波斯猫简介_波斯猫价格 > 波斯猫简介 > 墨香文学第十八期飘短篇小说常忆那年

![]() 当前位置: 波斯猫简介_波斯猫价格 > 波斯猫简介 > 墨香文学第十八期飘短篇小说常忆那年
当前位置: 波斯猫简介_波斯猫价格 > 波斯猫简介 > 墨香文学第十八期飘短篇小说常忆那年
我为什么会爱上他?说来也巧,就是那次爬香山,伙伴们在楼下喊我,我正在洗澡,匆忙中,只穿了长裤,锁门时,我看见那条粉色的内裤挂在衣架上。爬到山腰,一个趔趄,裤子的中线,从前开到后,羞死人了,十七岁的我,一个女生的前后,完全暴露在宇辉面前。
当时的他有些吓傻了,两眼直直的盯住了我的那个地方。经我大叫一声;“你看什么!”他才回过神来,脸色红红的。
他看了一下我的窘态,他忙着解开自己的上衣扣子。
我吃惊地问:“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可不要胡来啊!这还有别的同学!”
他脱下外衣又脱下衬衫,拿他那好看的花格衬衫衣给我象裙子一样围在了我被撕破了的裤子外面。他边围边说我:“小心眼”.
我们的故事也就由此开始了。
我,米桑,有点大大咧咧的个性。男孩子在我眼里,从没觉得神秘,我待他们如兄弟。
那年秋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宇辉,还有烟霞,青儿,如风,相约去爬香山。那年在青春的日记上标记着我已经才十七岁。
我骑着老爸给买的最新款红色的斯塔特斜梁车,我织了一对嫩绿色的把套,拴上一对毛茸茸的球球,走起来,像两个俏皮的玩偶,上下波动,俏皮讨喜。
今日看来,那时的我,依然充满孩子气。别看我已没心没肺的长到了公分。
青儿没有自行车,非要嚷着坐在宇辉的大梁上。
“华宇辉,今天赖定你了,必须带着我,谁让你们都长着两条大长腿。”
真赖皮,懒就懒呗,非找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我们见惯了她欺负他的事情,一点不惊奇。
青儿,一点没有青花的沉默,倒像极了青蛇的顽皮。
就这样我们一路欢笑着飞到了香山。
我穿着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裤,黄色的蝙蝠衫。我不知道我犯了一个最大的错。那条裤子惹了祸。
青儿大声喊着,喘着粗气,嘴里碎念着老天的不公,为什么给了我一条大长腿。而欠了她一截。让我停下来等等她。
我笑她吃东西挑食的劲头,和我养的波斯猫有一拼。她会跳起来偷袭我,怕痒的脖子。那时,我们疯起来,没有半点淑女样。
青儿指着我的长腿说:“米桑,就你这修长的腿,不当模特白瞎了。坏笑着说,要是你坐在宇辉的大梁上,都得掀起沙尘暴。”
而她,坐上,像个没发育完的小女孩,晃来晃去。
我说:“我不稀罕。自己骑,多拉风。”
宇辉笑着说:“带了个会动的布娃娃。”
我们都知道,宇辉把她当成了邻家妹妹。
是的,和一个人有没有故事,也许,只要十分钟。
宇辉回头看我时,我正心花怒放的香汗淋淋的跟在他后面。我不知道,是什么惊到了他,他的脸瞬间象山顶的红叶,我在他眼里看到了刹那的惊喜和驿动。那一刻,我想我是长在他的的眼睛里了。
后来他说,那时的我,黄色的蝙蝠衫,修长的身材,一头小鹿纯子的发型,象一只灵动的蝴蝶飞到了他的心里,有那么一刻,他几乎要停止了呼吸。而我两边奔走起来翘动的小辫子,清纯俏皮,多年后,始终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
一部电影里有句台词,我记得很深;当你遇上你的挚爱,时间就会暂停。
后来,宇辉在日记里写到,一种窒息的美,瞬间嘭上了心头,从那蝶舞的黄色衣衫掠过的那一刻,他的心就跟着一直起伏,直到回到寝室,那一瞬间的回眸仍在梦里缠绕,掠过身前,又会跑到身后。活了十七年,头一次对异性产生了萌动。
宇辉是那种在男孩堆里说话有分量的人物,男孩子都有点怕他。有种大哥的架势,对人却很温和。
我老觉得他身上有种江湖的味道。
那年,空巷无人,吃过饭后的人们都猫在家里等着看《上海滩》。街上流行黄色的程程衫。针织的一种开衫。我也有。
烟霞的苹果脸泛着花痴问到;“他怎么那么像文强啊。”
“他,是谁啊?”我明知故问。
“你就装吧,你数数,咱班谁不喜欢他?大众情人。”
“也就你把他当哥们吧。”
我知道,有很多女生在他面前甘愿低眉。
是的,我不怕他,因为我见惯了这种阵势,我爸爸就是一个站在那里即使不说话都让人敬畏的军人。
只是他们都不知道,他还是个独断独行的部长。
老天不知为何下起了小雨,兴致正浓的几人,急急地奔下山。还是那刮我裤子开线的地方,脚下一滑,一屁股摔在泥塘地,当我重新站起来之后,我那开线裤子外的围裙子掉了下来,我的前、后又一次地暴露给一起来爬山的同学。
天哪,这回可没脸见人了,怎么办?
宇辉又上前,闭上眼睛,帮我系上掉下来的他的衬衫,我的裙子。可是上衣终不能当下衣穿,系上扣子迈不开步,解开扣子不是前露,就是后露。
正在这为难之际,我一眼就看到了平时最要好的同学青儿的衬衫兜里即鲜红又明晃晃的百无大票儿。
我说让她借给我,让人下山到服装店先给我买条裤子,可她支支吾吾的不想借我,我知道,她想让我出丑。我闻到了一股醋味。借此机会我们一群人都在一棵伞状树下停下来。
宇辉说:
“我口渴了,谁有钱,拿出来给我,我要去买冰茶和饮料!”
青儿这时很爽快地拿出了百元大票儿递了过去。
这下可气死了我,
“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帅哥儿吗,异性相吸!”
在这时我就下决心,要把宇辉夺过来,我要嫁给这个看过我隐私的男人。
宇辉并没有拿着青儿给他的百元大票儿去买冰茶和饮料,而是到了山下旅游区大门外给我买回来了外裤。虽然内裤很漂亮,但是当这些人的面我如何把开线的裤子换下来呢?
青儿又在给出主意了,她显然是要报复我,她说:
“我们这几名女同在外站成人墙,围成圈,就让帅哥儿在里面帮着脱,帮着穿。”
说完不等别人笑她却先坏笑起来。
我想了想也来了馊主意,说:“那就不如我们现在就开始跳裸体舞,大家一起的脱,又一起的穿,这样即公平又不伤和气。”
说完大家嘻着,笑着,打着闹着。
宇辉不同意这样做,他也知道我们不可能这样做,他说:
“看,看,说疯还真要疯起来,我都不流氓,你们却要流氓了,你们真要是这样做,那我的相机可要派上用场了”
有两个女孩子一回也没有发言,这回她俩可急了。她说:
“你敢,我可不想上头条。”
青儿这回正而八景的说: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总该想出个办法来呀!”
宇辉说:“这里就我一个男孩,我躲开不就行了。”
“这道是个办法。”
就在宇辉走开之后,我解开了裤带,退下中线开缝的裤子。突然青儿恶作剧地喊道:
“蛇!蛇!蛇!”
她一惊一炸,大家都跑开了。
宇辉为了保护我又跑了回来。这时青儿却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大家才知道又上了青儿的当。我的下半体完整无余地暴露在“帅哥儿”面前。
宇辉慌忙用双手捂住了他的双眼嘴里忙说: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慌忙又提上开了中线的裤子,一想这样不行,在这山坡上换裤子时间需要太长,万一要是有人看见……
后来还是宇辉出了主意,说到山下卖服装的试衣室去换,经他一说,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除了我以外,青儿她们都一蹦一跳地向山下走去。
宇辉没有同她们一起走,他始终走在我的后面,为的是要保护着我。
从香山回来后,我刻意躲着他。尽管每次听到他嗒嗒的脚步声,我就心慌意乱,不知所措。
我觉得在他面前我变得透明了。我耿耿于怀,又心存感念。
而他,在我面前也变得大方不起。
我买了一条黄色的手绢,连同那条洗好的格子衬衫,还给了他。
后来我每次看高仓健的《幸福的黄手帕》时,眼睛里总下雨。我的忧伤来自那年的雨季。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狗血的事件。我们的关系明朗化了。
多年后,宇辉回忆起来,仍会面红耳赤。
我带了一包傻瓜瓜子,揣在裤兜里。我分给了几个好友吃。宇辉过来伸出了手;“米桑,我的那份呢。”
我喜欢看他打球的帅气。他从操场搭着他的外套才回来。
“自己掏。我两手正忙着呢。”
我感觉到有只手碰到了我的腿骨一侧,一股酥麻的东西,穿过头皮。
“笨死了,我掏吧。”我的脸飞过一朵云霞。
我看到了宇辉尴尬的瞬间。他误掏了我们那时还是旁开门的裤门。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的女性连裤门都是保守的。
我们的恋情怎能不夭折。
我要不是知道他是个坦荡的君子,此时,他的脸上一定会长着我五指的爪印。可那时,他的脸像一块被血殷红的纱布。不知所措的走开了。
我追上去递他瓜子的时候,他的尴尬模样还未退去。
恳切的眼神写满无辜,懊悔的表情。尴尬的不知把那只犯罪的手放到哪里。
磕磕巴巴地说;“米桑,我不知道我怎么会那样,我不是故意的,请相信我。”
我瞪了他一眼;“知道你是误掏错了,要不,你的脸上早印上了我的五指。”
别看我说的轻巧,回家后,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轻率的就原谅了他。
他不会想我我是个轻浮的女子吧?
尽管我对他并不反感。
我承认我有点喜欢他。
有那么一刻甚至妒忌过他和青儿的不拘小节。
从我见到他的那一刻,我少女的心扉就偷偷的开启着。
我喜欢他的的笑,他的稳重,还有他的成熟老道,都是我米桑世界里未来白马王子的典范。
他一定不知道,那洁白的牙齿笑过后,旁若无人中夹杂着的肆无惮忌,已悄悄的烙印在了一个女孩的心里。
是呀,谁都会要命的喜欢,却说不出理由。就是爱看了,他的笑,他的坏,他的超出年龄的稳重和淡然。还有一种不可一世的骄傲。
可我不能说啊。少女的矜持,怎么开口啊。
在没有这么好的欢喜了。
恰巧,原来,你也是在这里。
我也在你的眼里。
他约了我。
“米桑,我在眼镜湖边等你。不见不散。”
他拿准了我会赴约。我的小心思,没能穿过他的眼睛。
谁说的啊,心有灵犀一点通。
只是后来身无彩凤双飞翼。
眼镜湖边,我们蹬着铁皮船,有夕阳的斜晖打在身上。有水在船头追逐白色的浪花,一层层。
他喜欢听我说话,只静静的听着。我的脸泛成了一朵桃花。妖艳动人。
“打把伞吧,谁让白娘子遇到了许仙。”他调侃着。
“我可不做什么白娘子,一辈子压在塔下受罪。我只当一尾自由自在的鱼。”
我们说着所有恋爱中的人说的傻话。
我们开始了约会,我们恋爱了。
那时的云,真白啊,天也是瓦蓝瓦蓝的颜色。每走过的地方,好像都有花儿要开。
在我们眼里,世界好像只剩我们两个。一草一木,都在享受我们的甜蜜。连空气都变成一首首诗,游动着。
时间总是流逝的太快。心中的山水好像永远看不够似的。我们都盼着明天的约定早些到来。
我喜欢吃麻辣豆腐。宇辉从不吃辣的。每次吃时,他总在旁边看着我辣的哧哧的样子,傻笑。
“我将来要嫁个小四川人,天天解馋。我的嘴里飘着辣气。”
宇辉就会夹起一大块塞到我的嘴里。试图堵住我气他的嘴。
他夹起一片翡翠菜叶,滋滋的吧嗒着。“有什么好吃的呀,满嘴的醋味。”我襟着鼻子,嘟着嘴,拧着他的耳朵窃笑。爱吃醋的男子。
他爱吃醋溜白菜。我知道,像初恋的味道。酸酸的,甜甜的。
我不知道少年的青衫是如何一点点印染了少女的芳心,一次回眸,恋其一生。
象所有懵懂的故事一样,我们都成了彼此眼中最完美的那个人。
言情小说中的人,好像都换成了我们的容颜。那时的爱,单纯的象栀子花的颜色。一尘不染。
我的眼里,只有他。
他的眼里,再没有别人。
喜欢一个人,当真没有任何具体的理由么?没有。也就那么一颦一笑,一个招牌的举动,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坏笑。够了,这些已经足够了。喜欢当真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宇辉写了小纸条给我。我们约定在小河边桃花树下相见。
一床凌乱的衣衫,被翻来翻去。还是挑拣了那条白色的汗衫,白色的球鞋,蓝格子的裙子。我像一只蝴蝶飞了出去。在早春,有一只茧儿破裂了,似一只小猫儿的情绪在春天里蠕动。
那晚的桃花真粉啊。他分不清哪个是桃花,哪个是我的脸。
他的唇贴了过来。
我们像两个惊慌的小鹿,他的舌尖碰到我嘴里的那刻,我几乎瘫软在他的怀里,他的吻缠绵过后,最后狠狠地咬在我的舌头上,好像没有下次一样。笨拙的吻,几乎咬到了对方的牙齿。
那晚,宇辉吻了我,而我的初吻就这样在青春里丢失,无悔。
我们的恋情被肆意的渲染着。宇辉和米桑好上了。传遍了校园。
如风的大嘴,我捂不住。这个来去如风的坏小子,走到哪里,不忘介绍,我是他大嫂。
我能感到我风似的走过后,那些嫉妒,幽怨,还有羡慕的目光,杀过来。我的后背有一丝凉。
在没有男生敢刻意的靠近,宇辉的眼神,他们伤不起。霸道。独尊。他还有个牛气的外号,惹不起。
我叠满了满满一瓶紫色的星星。那里镶嵌着我们走过的每一个日子,都充满了缤纷。有粉红的回忆在那年的夏日里盛开。
那年的大街小巷都在卡带中唱着齐秦,童安格,姜育恒的歌。
我不知道爸爸怎么会来到学校,一定是我泛着桃花的脸出卖了我自己。这一切,瞒不过身经百战的老爸。
那晚,家里空气象外面阴冷的天。
“明天我给你转学。不要让我知道你还和那个穷小子联系。”我叫他老头。老头的青筋暴涨着。
“我都满十八了。我有自己的选择。”我嚷着。
“一个不能给你将来的农村人,我不同意。”
“农村怎么啦,你还不是吃着他们种的饭长大的。”
这是我长大以来,第一次反抗,我们都挑着世上最毒的话反击对方。
我记得那晚爸爸摔坏了好多青花的碗。那是他特真爱的东西。他一直将我公主似的供养着。为了一个男孩,我顶撞了他。
我狠狠的将一只蛾子拍在了雪白的墙面上。盯着那团黑点,不肯入睡。
我的爱,刚要沸腾。就被沏灭。我懵懂的心,还在萌芽,它试图穿过层层跺墙,泛绿。
感情就是像他说的那样,越是压迫,越是反抗。
我们偷偷的约会。
我盼着那个时刻快到。
宇辉说,他也被他父亲臭骂了一顿。说,让他好好读完大学,出人头地。癞蛤蟆只有变成青蛙,才能找到白天鹅。
多年后,我迷上了陈瑞的那首。
最后的那一片枫叶
了断了尘缘空阙
坠落在缠绵的深渊
憔悴在风花雪月
最后的那一片枫叶
作别了西窗楼雪
消失在茫茫的荒野
沉睡在冰冷世界
多少次我踏遍寒山
寻觅你的多情笑靥
多少次我凝望远方
幻想你的独影摇曳
你飘逸的身影
宛若是一只香殒的蝴蝶
你赤红的凋落埋葬了
一季相思的誓约
没有他的世界,我已一片荒芜。
宇辉喜欢我的长发,后来,我一直留着。
他说,我的头发有薄荷的香味。
只是不知我所为留长发的人,如今他又在哪里呢?
我到底被爸爸带到了香港,我的小胳膊终没有拧过大腿。
那时,我和宇辉相处了两年。大学那年最后在香港学完了学业。
后来,青儿告诉我,我离开后,宇辉的颓废和沮丧。
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
那时,宇辉颓废的只有这两句话适合。心灰意冷,天昏地暗,在没有花开和明艳在他眼里。
夭折的恋情,令人绝望。
我的泪那年掘了堤,淹没了青春。从此,白色的花,成了最爱。
一切,像一个梦,梦里落花缤纷。
我结婚了,留在了澳大利亚。我的丈夫是个房地产富商。可我再也没有那样的爱了。
我常回国打理生意。
老公有了外遇。我选择了离婚。
那个被我唤作笨蛋的人,始终坐牢了心头,不肯淡化。
后来,一个如我容颜的女子,待他走出了情殇,做了他的妻子。
那年那场栀子花般的初恋就这样定格在我的青葱岁月,与我梦一般的妖娆着。
而有时,我多希望,那年,我们只是不小心走散。
作者简介:飘,原名马静,70后,赤脚自由人。喜爱在烟火中打磨墨色。曾用名飘飘飘,焚心止水,游走于网站发文。偶有小说上刊。推荐社长:古垒东边
转载请注明:http://www.logistics-info.com/bsmjj/11840.html